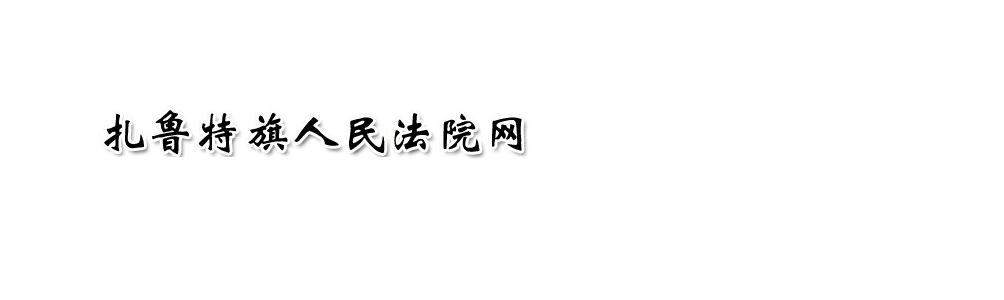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这是为了弥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定得过于原则、简单的缺失,为了满足诉讼实务中规范当事人和法官运用证据的行为的需要而出台的一项审判制度。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法官释明,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为了明了诉讼关系,通过就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向当事人发问的方式,促使当事人作出进一步陈述或者补充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目前,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自己在日常生活所遇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纳,那么人们应采取怎样的诉讼行为才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在诉讼中举证,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指导当事人举证,是法官释明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规定举证方面的释明义务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具备律师强制代理的条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要求当事人必须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在诉讼实务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由其本人进行诉讼。这样的当事人一般都既缺乏法律知识,又不熟悉诉讼程序,他们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的规则很陌生,如果法官不做举证方面的释明,很可能造成一些当事人仅仅因为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误解或者不知如何举证而败诉,其结果是本来应当胜诉的当事人只是由于不熟悉证据规则而未能获得正义。这样的结局显然是有悖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宗旨的。 考虑到我国的这一现实国情,《证据规定》明确要求法官在向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在通知书中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等。《证据规定》还规定了法院指定和当事人协商这两种确定举证时限的方式。但问题在于,虽然《证据规定》设定了两种确定举证时限的方式,但实践中采用的多数是由法院指定。造成确定方式单一化的原因在于:
首先,第一审民事案件大多数是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而基层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适用的是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一般流程是只开一次庭,原告起诉,被告答辩,接下来便开庭审理,很少在开庭前安排一个用于确定争点、固定证据的审前准备程序,缺乏这样的程序,原、被告在开庭前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自然无从来协商确定举证时限。即便是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案件,法院多数也是采用指定的方法来确定举证时限。
其次,《证据规定》第33条的内容也使得法院倾向于采用法院指定的方式来确定举证时限。根据该条的规定,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除了应当载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外,还应当载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而对于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则是“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一个是“应当”,一个是“可以”,“应当”是要求调整对象做出积极行为的强制性规范,而“可以”则是一种带有授权性质的任意性规范,因此法院在具体操作时选择指定的方式解决举证期限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次、是我国法院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实行“立审分离”,立案工作由立案庭负责。受理案件后,向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是立案庭的工作职能之一,所以立案庭会随着举证通知书的发送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限。 采用法院指定的方法,确定举证时限的时间便被定格在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之际。法院受理案件后就指定举证时限虽然可以使举证时限早日确定下来,但在受理案件的初始阶段就确定举证时限的合理性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在这一阶段,法院所能够获得的案件信息是非常之少的。法院还未收到被告的答辩状,而法院从原告的起诉状中所获悉的,只是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但由于被告尚未答辩,法院并不清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不清楚双方争议的究竟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具体地说,在这一阶段指定举证时限带来的问题是,法院在举证通知书中对当事人所做的举证指导只能是脱离本案的一般性指导,而不是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形所作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指导。例如,原告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所借的款项。法院在举证通知书中须载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和要求,法院在作这方面的指导时,只能根据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情形告知原告应当对双方对借款意思表示一致的事实和原告将出借之款交付给被告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应当向法院提供这两方面的证据;而对于被告,也只能笼统地告知他应当对答辩所依据的事实负证明责任,最多也只能大致地告知被告可以主张清偿、提存、抵销、混同这些引起债消灭的事实并负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被告的答辩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他可能主张原告交付给他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货款或租金,或是原告为履行合伙义务而提供的出资款,也可能提出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抗辩。